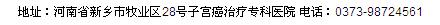死亡有一万扇门,你在哪扇门前谢幕一己
”陈小鲁一直后悔没有帮父亲有尊严地离开。陈老帅病重到最后,已基本没有知觉。气管切开没法说话,全身插满了管子,就是靠呼吸机、打强心针来维持生命。“父亲心跳停止时,电击让他从床上弹起来,非常痛苦。”陈小鲁问:“能不能不抢救了?”医生说:“你说了算吗?你们敢吗?”当时,陈小鲁沉默了,他不敢作这个决定。“这成了我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。”开国上将张爱萍的夫人李又兰,了解罗点点和陈小鲁倡导的“尊严死”后,欣然填写了生前预嘱,申明放弃临终抢救:“今后如当我病情危及生命时,千万不要用生命支持疗法抢救,如插各种管子及心肺功能启动等,必要时可给予安眠、止痛,让我安详、自然、无痛苦走完人生的旅程。
”年,李又兰病重入院,家属和医生谨遵其生前预嘱,没有进行过度地创伤性抢救,李又兰昏迷半日后飘然仙逝,身体完好而又神色安宁,家人伤痛之余也颇感欣慰。“李又兰阿姨是被生前预嘱帮到的第一人。”罗点点很感动。
经济学人发布的《年度死亡质量指数》:英国位居全球第一,中国大陆排名第71。何谓死亡质量?就是指病患的最后生活质量。英国为什么会这么高呢?当面对不可逆转、药石无效的绝症时,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。何谓缓和治疗?“就是当一个人身患绝症,任何治疗都无法阻止这一过程时,便采取缓和疗法来减缓病痛症状,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,让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完满有尊严。”
缓和医疗有三条核心原则:
1、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;
2、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;
3、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。
英国建立了不少缓和医疗机构或病房,当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经无法治愈时,缓和医疗的人性化照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。这时,医生除了“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症状的办法”外,还会向患者家属提出多项建议和要求:
1、要多抽时间陪病人度过最后时刻。
2、要让病人说出希望在什么地方离世。
3、听病人谈人生,记录他们的音容笑貌。
4、协助病人弥补人生的种种遗憾。
5、帮他们回顾人生,肯定他们过去的成就。
…………
肝癌晚期老太太维多利亚问:“我可以去旅游吗?”医生亨利回答:“当然可以啊!”于是维多利亚便去了向往已久的地方。
中国的死亡质量为什么这么低呢?一是治疗不足。“生病了缺钱就医,只有苦苦等死。”二是过度治疗。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接受创伤性治疗。尤其是后者,最让人遭罪。
医院原肿瘤科主任刘端祺,从医40年至少经手了例死亡病例。“钱不要紧,你一定要把人救回来。”“哪怕有1%的希望,您也要用%的努力。”每天,他都会遭遇这样的请求。
他点着头,但心里却在感叹:“这样的抢救其实有什么意义呢!”在那些癌症病人的最后时刻,刘端祺经常听到各种抱怨:“我只有初中文化,现在才琢磨过来,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。为治病卖了房,现在还是住原来的房子,可房主不是我了,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……”
还有病人说:“就像电视剧,每一集演完,都告诉我们,不要走开,下一集更精彩。
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,尽管主角很想活,但还是死了。
”病人不但受尽了罪,还花了很多冤枉钱。数据显示,中国人一生75%的医疗费用,花在了最后的无效治疗上。有时,刘端祺会直接对癌症晚期病人说:“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。”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。没多久,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。又没多久,病床换上新床单,人离世了。
医院,刘端祺最不愿去的就是ICU,尽管那里陈设着最先进的设备。“在那里,我分不清‘那是人,还是实验动物’。”花那么多钱、受那么多罪,难道就是为了插满管子死在ICU病房吗?
穆尤睿做梦都没想到,自己的文章会在美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。这篇文章让许多美国人开始反思:“我该选择怎样的死亡方式?”美国人约翰逊看完这篇文章后,立即给守在岳母病床前的太太打“现在才知道,对于临终者,最大的人道是避免不适当的过度治疗。
不要再抢救了,让老人家安静离开吧!”太太最终同意了这个建议。第二天,老人安详地离开了人间。这件事,也让约翰逊自己深受启发:“我先把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写下来。将来若是神智清楚,就算这是座右铭;如果神智不清了,就把这个算作遗嘱。”
于是,约翰逊写下了三条“生前预嘱”:
1、如果遇上绝症,生活品质远远高于延长生命。我更愿意用有限的日子,多陪陪亲人,多回忆往事,把想做但一直没做的事尽量做一些。
2、遇到天灾人祸,而医生回天乏术时,不要再进行无谓的抢救。
3、没有生病时,珍惜健康,珍惜亲情,多陪陪父母、妻子和孩子。
随后,约翰逊拨通电话,向穆尤睿征求意见。穆尤睿回答:“这是最好的死亡处方。”
当我们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时,是像约翰逊一样追求死亡质量,还是用机器来维持毫无质量的植物状态?英国人大多选择了前者,中国人大多选择了后者。
这是上海“丽莎大夫”讲述的一件普通事,之所以说普通,是因为这样医院发生——一个80岁老人,因为脑出血入院。
家属说:“不论如何,一定要让他活着!”4个钟头的全力抢救后,他活了下来。不过气管被切开,喉部被打了个洞,那里有一根粗长的管子连向呼吸机。偶尔,他清醒过来,痛苦地睁开眼。这时候,他的家属就会格外激动,拉着我的手说:“谢谢你们拯救了他。”家人轮流昼夜陪护他,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上的数字,每看到一点变化,就会立即跑来找我。后来,他肿了起来,头部像是吹大的气球,更糟糕的是,他的气道出血不止,这使他需要更加频繁地清理气道。每次抽吸时,护士用一根长管伸进他的鼻腔。只见血块和血性分泌物被吸出来。这个过程很痛苦,只见他皱着眉,拼命地想躲开伸进去的管子。
每当这时,他孙女总低着头,不敢去看。可每天反复地清理,却还能抽吸出很多。我问家属:“拖下去还是放弃?”而他们,仍表示要坚持到底。孙女说:“他死了,我就没有爷爷了。”
治疗越来越无奈,他清醒的时间更短了。而仅剩的清醒时间,也被抽吸、扎针无情地占据。他的死期将至,我心里如白纸黑字般明晰。便对他孙女说:“你在床头放点薰衣草吧。”她连声说:“好。我们不懂,听你的。”第二天查房,只觉芳香扑鼻。他的枕边,躺着一大束薰衣草。他静静地躺着,神情柔和了许多。十天后,他死了。他死的时候,肤色变成了半透明,针眼、插管遍布全身。面部水肿,已经不见原来模样。
我问自己:如果他能表达,他愿意要这十天吗?这十天里,他没有享受任何生命的权力,生命的意义何在?让一个人这样多活十天,就证明我们很爱很爱他吗?我们的爱,就这样肤浅吗?
年,80出头的学者齐邦媛,离开老屋住进了“养生村”,在那里完成了记述家族历史的《巨流河》。《巨流河》出版后好评如潮,获得多个奖项。但时光无法阻止老去的齐邦媛,她感觉“疲惫已淹至胸口”。一天,作家简媜去看望齐邦媛。两个人的对话,渐渐谈到死亡。“我希望我死去时,是个读书人的样子。”
最后一刻仍然书卷在手,最后一刻仍有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的优雅,最后一刻眉宇间仍然保持一片清朗洁净,以“读书人的样子”死去,这是齐邦媛对自己的期许。你呢?如果你是绝症患者,
当死亡不可避免地来临时,你期待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人世?如果你是绝症患者家属,你期待家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人世?
不久前,浙江大学医学院博士陈作兵,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后,医院进行放疗化疗,而是决定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——和亲友告别,回到出生、长大的地方,和做豆腐的、种地的乡亲聊天。他度过了最后一个幸福的春节,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,7菜1汤。他给孩子们包的红包从50元变成了元,还拍了一张又一张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。 …………
最后,父亲带着安详的微笑走了。父亲走了,陈作兵手机却被打爆了,“很多人指责和谩骂我不孝。”面对谩骂、质疑,陈作兵说:“如果时光重来,我还会这么做。”尼采说:“不尊重死亡的人,不懂得敬畏生命。”我们,至今还没学会如何“谢幕”!
来源:李银河本文仅供学习交流,部分文章推送时未能与原作者取得联系。若涉及版权问题,敬请原作者与本公号编辑联系删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