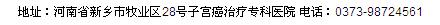我老公和小三车祸意外去世,他们留下六岁的
我从小就知道自己将来要嫁的人是谁,就是我的哥哥周凯默。因为他不是我的亲哥哥,而是我养父的儿子。
我刚生下来时有先天性心脏病,被拉三轮的爸和擦皮鞋的妈放弃,然后被好心的养父带回家抚养,养父对我很好,当亲生女儿一般疼爱,我还有了一个哥哥——凯默。而养父给我取的名字,则叫凯琴。
凯默总是穿着干净的深蓝工作服,身上一股好闻的肥皂水味道,对我非常宠爱。所以,当养父有意想要撮合我俩时,我的心里满是欢喜和期待。我对凯默的爱情,从十五岁那年就开始滋长。
在明确了养父的意图后,凯默一改往日的温厚,开始慢慢变得沉默,不爱回家,回家也不搭理我,甚至还训斥我。凯默很明显地在嫌弃我,我不知道该怎么办,只能沉默地等待,我感觉自己等待的姿势像一支风中的芦苇草,虽然被吹得东倒西歪,却始终根植于泥土。
两年后,凯默开始做生意,因头脑灵活和手脚勤快,他的生意越来越上轨道,家境也渐渐宽裕起来。这时,养父见时机成熟,又来催促凯默和我的婚事,凯默终于与父亲爆发了战争。当他看见缩在墙角瑟瑟发抖的我时,便走上前恶狠狠地说:“我不会和你结婚的,你死心吧!”然后摔门而去。
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养父也没想到凯默竟然如此坚决,也许他担心这样纠缠下去对大家都不好,所以他叹着气对我说:“琴儿,等爸给你另找户好人家吧。”
这天,我在房间里哭了一夜,也思考了一夜。我想我不能就此失去凯默,失去我的爱情。
第二天深夜,凯默在外面喝了点酒回来,醉醺醺地往床上一躺时,却猛然触到一个柔软的身体。他一个激灵,酒立刻醒了,腾地坐起来就去拉房间的灯却看见我只穿了一件内衣。
凯默第一个反应就是闭上眼睛,第二个反应就是别着头向外冲,我急了,大声叫住他,你敢走,我就告你非礼!
凯默用被子把我包起来往床下拉,我挣扎着跟他撕扯,弄出很大的动静。凯默气急之下给了我一个耳光。我摸着半边火辣辣的脸,声嘶力竭地哭起来。
养父被响声惊动,推门便见我和凯默在床上撕打的场面,我衣衫不整,哭哭啼啼,场面十分不堪。
我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整整三天,终于换来了养父一句比石头还硬的承诺,如果不让凯默娶了你,保全你的清白名声,我就死在他面前。
然后凯默妥协了,因为养父有心脏病和高血压,受不了刺激。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嫁给了凯默,我以为我从此会过上梦想中的生活。
其实,我也知道自己的婚姻是骗来的,我知道凯默为此背负了多大的屈辱和委屈。
凯默买了新房子,迫不及待地搬离了原来的小弄堂,他需要一个陌生的环境,来舒展自己憋屈的人生。我则像所有对未来充满幻想的新婚妻子一样,兴高采烈地盘算:“这里要放一套沙发,晚上我们可以窝在里面看电视,那里要一面窗帘,免得一大早阳光就照进来了……”
我在新房子里欢天喜地地折腾,将家具来来回回地搬弄,把桌子和地板擦得纤尘不染,却换来凯默一句冰冷的话:“你不要动我的房间,我自己收拾。”
凯默的话像铁锤一般敲醒了我的大脑,自从结婚后,他就没再搭理过我,更让我难以启齿的是,他从来就不碰我。他每天都回来得很晚,然后在沙发上倒头便睡。我一个人躺在新婚的大床上,感觉自己像一片沙漠,在他的冷漠里,慢慢地干枯和风化。
现在,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新房子,而凯默却要单独的一间卧室。
我的愤怒和伤心在一瞬间被点燃,我悲愤地冲着他大喊:“你到底想怎样?”
凯默看都没有看我一眼,就摔门而去。
凯默每天都很晚回家,除了必要的交谈,他几乎不和我说话。他的生意越做越好,我便做起了全职太太,只是家里太空,所以我经常回去陪伴养父,哪怕陪养父听收音机,看着他打盹,也比回家呆在空屋子里强。
可是不久后,养父因脑溢血去世了,我在那一刹那万念俱灰,因为连最后可以陪伴我的人都没有了,我将开始久远的孤独。
我开始明白自己的婚姻是一场错误,就像一个演员被推上了前台,炽烈的聚光灯都打在我一个人身上,所以我只能持续表演,不能退场。
凯默这时却有了不寻常的动静。先是一个闺蜜告诉我,亲眼看见凯默的车里坐着一个女人。再后来,连周围的邻居都在指指点点。我后来才惊奇地发现,那个女人竟然就住我家楼下。
那个女人并不比我更年轻或者更漂亮,她的丈夫生病去世,她独自抚养着一个六岁的女儿。凯默大概在一年前和她相识,后来便明目张胆地来往。
我真的不甘心,我的爱情从十五岁那年开始,这么多年未曾停息,只是这爱生生地被阻断,堵截,早已在心里郁结成塔。如果可以,我倒希望自己能洒脱地放手。只是,我不知道从哪里去找这么一股力量。
终于有一天,凯默一声交待都没有,就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搬到了楼下女人的房子。当凯默这么做的时候,我拉住他的手哀求:“你好歹给我留一点脸面。”
凯默摇摇头,仍旧摔门而去。
我在那一夜割腕,可是我没有死成,医院醒来时忽然就醍醐贯顶,忽然觉得自己的坚持毫无意义。所以我对前来看望我的闺蜜说,我要离婚。
可是我没想到,我居然连婚都离不成。
在我出院的第二天,凯默与楼下那个女人开车行驶在高速路上时,被一辆大货车撞得面目全非。
当时我正在厨房炖一只鸡,用小火慢慢地熬,厨房乃至整个屋子都溢出浓郁的香味。我打算请楼下那对男女上来吃一顿饭,然后宣布离婚的决定。
因为凯默的影响,那个女人对我是不屑一顾的,从来就昂着头进进出出,想来她认为像我这种利用欺骗获得婚姻的女人,并不值得同情。
放手也罢,成全也罢,这都不重要了。只是我还应该对凯默道一个歉,要不是自己当年的任性和唐突,也许今天我和他的人生,都是另外一种样子。
电话在这时响起,我的心一点一点的,由安宁到茫然,再到虚弱的失控。
办完了凯默的后事,我领养了楼下那个女人的女儿,她只有六岁,还不太明白死亡是怎么回事。我给女孩买漂亮的衣服,时髦的玩具,女孩最初是怯怯的,后来便活泼起来,三个月后的一天,她冲我叫了一声“妈妈”。
我不怪凯默,他和我一样,都是为了爱情赶路的人。只是我们天生不该是夫妻,所以永远交汇不到一个点上。收养这个孩子,也许是为了某种救赎,又也许,我因为这个孩子而得到了慰藉,否则,便只能任由自己的心灵夜夜奔突,不得安宁。
北京看白癜风医院哪里最好北京治疗白癜风去哪个医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