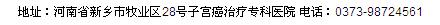追债记之回家回家
在这里,各式各样的人,生着各式各样的病。医生们尽力治疗,病人们努力康复,一切,似乎就该这么纯粹。然而,事实总比想象要复杂得多。一些看似与治疗无关的问题常横亘医生面前,再高明的医术解决不了,也无法绕过。
九月下旬的江南,暑热逐渐消退,大中午即使不开空调,室内的温度也能让午休时间过得气定神闲。忽然,手机铃声不合时宜地扯开了嗓子:“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……”
电话那头,是ICU左主任。“我这里有个病人,脑出血术后,病情很重,进来十天了,家属来过一次后就不来了,怎么办啊?”
很显然,这又是一个被家人有意抛弃的病人。
丁华东,39岁,四川人,在杭州打工,医院四五公里外的一个小镇。十天前的清晨,他在出租房里不省人事,医院。
医生诊断为大面积脑出血,深昏迷,不立即手术必死无疑,马上开颅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当时他身边没有家属,在警察的见证下,医院总值班代替家属签了手术同意书,为他做了急诊开颅手术。
派出所根据身份信息很快找到了他家人,第三天,医院。丁华东处于昏迷中,插着呼吸机,嘴张得老大,双眼浮肿,脸部扭曲变形,看上去有些吓人。
“这是一场大病,积极治疗应该能够醒来,但或许会留下明显的后遗症,生活能不能自理要看后期康复情况。治疗我们会尽力,之前家属没来,医药费都欠着,现在你们来了,想办法把费用交上。”医生说。
他哥哥在丁华东身边默默站了会儿,离开了。接下来几天,医院。开始医生以为是因为工作忙或者筹医药费需要时间,直至那天,有个治疗方案需要家属签字,医生电话联系了他。有好的治疗办法,家属一般都是巴不得赶紧签字,他哥哥却拖了好几天都不来。
医生们感觉到了异样。
左主任在找我之前,已跟对方电话沟通了多次。“他一个人,没结过婚,出来十年了,从不跟家里联系,这些年都是自己赚钱自己花,现在出这事,我也没法管。”他哥哥表示已离开浙江,去了海南。
十天过去了,丁华东正在逐渐醒来,他脱离了呼吸机,已经能够自主呼吸。叫他名字,偶尔能睁开眼睛,只是眼神混沌散乱没有着落点,他的意识仍处于模糊状态。
命是保住了,但四肢功能都明显受到了影响,右边的手脚根本不能动,左手的活动力量也明显减弱。后期将面临的,是漫长的康复治疗,要完全恢复已不可能,最好预期是生活基本自理。也就是说,这个39岁的大男人,以后再也不能自己挣钱自己花,必须依赖别人才能活着。
公司里的人来看了一次,丁华东到那里上班才一个多月,刚准备给他买社保但还没买。就算买了社保,按规定医保也要六个月以后才能办,这就是说,他的医疗费用完全需要自费。这种境况下,谁沾上他,就是一辈子的负担,家人避之唯恐不及,其实也是有部分的不得已。
现在,摆在眼前的问题是,没有医保,没有积蓄,已欠费七、八万,后续还需继续治疗,这医药费丝毫没有着落。待病情稳定,他就应该转到普通病房,家属不出现,陪护没有着落。没有亲人,没有房子,没有生活来源,丁华东出院后的去处没有着落。一个原本扎根生活于芸芸众生的人,现在像一颗植物从泥土中被连根拔起,没有了任何精神和物质上的滋养,生命与未来变得飘忽起来。
我想来想去,想到了民政部门,这可是专们帮助困难人群的政府机构。打听到丁华东租住地民政办主任的电话,一看名字,竟然是我十几年前带过的一个学生。当年我是妇产科的助产士,她是一个乡镇的计划生育服务派来的进修生,专门来学习人流、放环、取环这三项计划生育小手术,因为年纪相仿,相互之间处得不错。
我心里很高兴,有这层交情在,能帮的忙应该不会不帮吧。果然,电话那头的声音依稀还能与记忆里的相匹配,只是多年未见,语气中已有了场面上的客气。
“我们的救助主要针对本地户籍人口,外地民工患重大疾病时,要有在本地打工满一年以上的证明,并由本人提出申请,我们可以考虑相应救助。”很明显,这些条件丁华东都不符合。
“既然他是厂里的工人,你可以找工会试试,他们有一笔救助工会会员的专项基金。”我赶紧从网上找来工会电话打过去,“如果他是工会会员,可由单位提出申请,年底可以得到两到三千元的困难补助。”两到三千元?杯水车薪啊,聊胜于无吧!再打“我们小私营企业,根本没有成立工会组织。”公司负责人说。
再打电话给民政办那位老相识,心里有点死皮赖脸死缠烂打的感觉。“要不你们找救助站试试吧,他们或许有办法。”她又给我出主意。
我感觉救助站是针对流浪汉的,既然没有别的路,那就试试吧,或许行呢。“如果他回老家有困难,我们帮他买张车票还是可以的,医药费就没办法了。再说他有家人,也不是流浪乞讨人员。”救助站工作人员说。
走了一大圈又回到起点。救助的机构和途径似乎很多,但救助力度都不大,大家还各自画了一个圆圈,规定了自己的救助范围,而这个丁华东,似乎正处于众多圆圈的间隙地带,不管哪方面的救助条件都够不着。
但这么一个急需救助的人,他就在这里,他比一般的生活困难没有路费回家的人更需要救助百倍千倍。当那些原意为了保障而制的规定,成为名正言顺拒绝救助的托词,
医院,无处可躲,无法推脱。一个人,一个有病的人,施以援手,他就可以活着,反之,他就陷入绝境。医院,此时充当了丁华东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,丁华东的记忆稍有恢复,能听懂简单的词汇。其间,派出所又多次跟他老家方面联系,得知他家中还有一个七十几岁的老父亲。那天查房,医生问丁华东,你想家吗?想父亲吗?他忽然双眼流泪,呜呜呜地哭出声来。在场的医护人员一阵心酸。
确实,医院不是他的家,医生帮他治病已经很不易,没有能力管他一辈子。因此,最好的办法还是帮他找回家人与亲情。但是,之前的种种努力,在现实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,医务人员人微言轻,只有想办法借助社会的力量试试。
那天,医院官方微博上发出一条讯息,“死亡线上挣扎22天,四川籍民工念家盼亲人”,并附上了丁华东躺在重症监护室病床上的照片。本地几个有影响力的媒体和公安机关的官方微博进行了转发,众多爱心网友纷纷帮忙扩散,两个小时点击率超过两万。消息很快通过网络传到了四川。下午,四川方面两家很有影响力的纸媒记者相继打来电话,详细询问丁华东的情况,希望社会舆论的力量能让事情有所转机,改变丁华东的处境。
四川的有家媒体记者赶到丁华东的老家。70多岁的老父亲,坐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破旧老屋前,手里编着一个竹筐。
老人有三个儿子,丁华东是老二,儿子们都在外打工,自己靠偶尔帮人打点零工艰难度日:“早就接到派出所的通知了,我实在管不了,请那边的好心人救救他吧,如果不行,我就当这个儿子死了。”记者打电话给他弟弟,“要是想去早就去了,如果去也就是去看看,治疗费啥的也负担不起。”
第三天,那家报纸以“打工男杭州病危盼不来亲情”为题,用整整两个版面对此事进行了报道。从法律法规、医保政策、社会救助角度,对在外务工者在他乡生病,老家的新农合能否发挥作用,如果亲属弃之不管是否违法,社会都有什么救助渠道等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。
最后的结论是,丁华东已经成年,父亲兄弟都不再有法定的抚养义务。他在外打工多年没有参加老家的新农合,无法享受医疗保障。当地律师还提出,所在地民政部门应当承担起救助的法定义务。问题又转了回来。
那家报纸还是非常有社会责任感,指出社会救助应该是社会保障的兜底线,医院已经躺了一个月,在高额的治疗费用前,除了不是慈善机构医院独自苦撑外,并没有其他任何部门伸手救助,说明国家的救助网存在盲区。
我们发出第二个微博“我们该怎样来拯救你,我的病人”,网友们纷纷出来说话:“此事非个案,捅伤的不是我们的心,而是社会保障的洞。”
“医院帮得了他一时,帮不了他下半辈子,帮得了他一个,帮不了一个群体。”
“我们的社会救助体系应该更加完善,让丁华东们身处困境不无助,让医生救人之后不无助。”
网络和纸媒上的讨论轰轰烈烈,本地两家电视台也一起介入,对这件事进行了系列报道。大家的谈论重点是,国家应该建立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,帮助有类似遭遇的在外务工人员度过难关。
但这一切,对丁华东来说,是迢迢之远水,解不了他火烧眉毛的近渴。眼前的问题,仍未得到切实的解决。
一阵秋雨一阵凉,季节进入深秋,窗外草木萧瑟。监护病房一年四季保持着人体最适宜的温度。丁华东头上的手术伤口和喉部气管插管的伤口早已愈合,但脑溢血后遗症状十分严重,右侧身体偏瘫无法下床,不会讲话,不能自己吃饭,大小便也不自知,生活完全不能自理。腿部肌肉消瘦萎缩,手指及手腕关节扭曲变形,因为开颅手术被取掉颅骨的部位明显凹陷下去,看上去有些不堪。
他的精神状况在逐渐好起来,一只手常乱抓乱动,嘴里发出“啊啊”的叫声。他有时会发脾气,不吃护工阿姨喂的饭,小护士喂他,他就吃。护士说:“不能发脾气,要听话,听懂的话就握一下手。”他就会用能活动的左手紧紧握一下护士的手。医护人员和护工照顾他大小便,给他喂饭喂水,教他说话,在他手里放一个乳胶小玩具,让他捏着练练手劲,还经常从家里带水果给他吃,把他当孩子一样哄着。
没有家属陪护,医生无法将丁华东转到普通病房,只能一直把他留在重症监护病房。因为监护病房是一个大通间,每班最少有三名护士在岗,二十四小时有护工,能及时照顾到他。而普通病房中,一名医生一名护士,夜间要管几十号病人,根本无法顾及一个瘫痪病人的生活。其实,医生也很明白,监护病房一共只有十二张床位,丁华东长期占用了一张,这是对公共医疗资源的浪费。
但除此之外,想不出更好的办法。丁华东病情稳定后,医院就每天安排康复科医生到监护病房为他做肢体功能锻炼,不能因为没有家属,而错过他康复的最佳时机。
转眼两个多月过去,按丁华东的病情,早就可以出院修养了,但他只能在监护室待着。医生给他换了一个靠窗的床位,因为长期在重症监护室,有被耐药菌感染的风险,那个位置离别的病人相对远一些,空气流通也相对好些,躺在床上还能看到外面的景色。
对于这一切,其实丁华东并不知晓,他的思维大部分仍是迟钝紊乱的,只有提起老家和家人,才会有快速明显的情绪反应。
院方已不再对家属抱有希望,也不再期盼有哪个部门能主动站出来帮助这个可怜人,但医院不是敬老院,不能养他终老,他总得有个去处。在杭州,他无法享受任何社会保障与救助,回户籍所在地,或许才是他最好的出路。
救助站、派出所,派出所、救助站,我们轮番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电话,请求,沟通,协商。
派出所说:“出警,救助,送医,协查,能做的我们都做了。”
“警察叔叔说话有威力,再帮忙想个办法说句话吧!”
确实,同样一句话,从医护人员嘴里说出来,别人会觉得是为了利益,由警察说出来,就代表着法律与正义。
“后续的事我们无能为力了。”
“救人救到底,送佛送到西吧,医院,医院该怎么办呢?”
“那我们请示请示领导吧。”救助站说:“病人我们是不能遣送的,半路病情发生变化怎么办?”
“我们可以派车送他到火车站,医生保证,他路上不会有生命危险”。
“我们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没有护理经验。”
“我们可以派医生全程跟随护送。”
沟通。等待。对于十几万的医药费,医院已完全不抱希望,因此也不再提起,只想给丁华东找一个归宿。又二十天过去,终于有好消息传来,派出所和救助站达成共识,与医院三方各派一名工作人员,护送丁华东回四川老家。同时,派出所联系了当地公安局,救助站也与当地救助站联系,他们答应到时会派车到火车站接人。
丁华东终于要回家了,医护人员告诉他这个消息,他又一次涕泗横流,呜呜地哭出声来。火车票就定在三天以后的上午十点。
医护人员着手为他准备行装。我们到街上为他买了新衣服,红色的,喜庆。新帽子,用来遮挡和保护他缺损凹陷的头颅。短裤买了四条,以免半路尿湿,新鞋新袜子毛巾餐巾纸湿纸巾尿不湿矿泉水面包,能想到的都买了,满满两大包。
那天一早,医生护士给丁华东脱下病人服,换上红衣服新裤子。丁华东兴奋地哇哇乱叫,伸出并不灵活的手,把新鞋子揽过去抱在怀里。
ICU左主任给他戴上新帽子,竖起大拇指,夸他很帅,护士把一面镜子拿到他面前,看到镜子里的自己,他竟然咯咯咯笑出声来。
原先对丁华东事件做过采访的市、区两家电视台得知消息,也赶来拍摄报道,在大家的簇拥下,丁华东被抬上救护车,在医生的陪同下赶往火车站。一名派出所干警,一名救助站工作人员已在火车站等候。
在异乡重病一百零六天后,丁华东终于踏上回家路。单趟两天两夜的行程,身体瘫痪、大小便失禁的病人,那场护送任务异常艰辛,但最终安全送他踏上了家乡的土地,把他交到他家乡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手里。他们说丁华东的老家在偏僻山村,要第二天才能送他回家。
一年之后,丁华东回乡的那个日子,护送他回家的郑医生跟我念叨:“丁华东不知怎样了,在偏远山区的那种医疗条件下,那样的家庭环境中,不知是不是还活着,家人护理得好不好。”
是啊,一年了,杳如黄鹤的丁华东,你在家乡还好吗?
湖南白癜风医院北京白癜风医院治疗